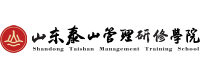爷爷的烟袋
时间:2014-07-31来源: 作者:
——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
在我的记忆中,爷爷一生没离开过他的宝贝烟袋。
一
那是一根极普通的烟袋:一尺多长,黄铜烟锅,玉白烟嘴,紫黑色的烟袋晶莹发亮。就是这样一根烟袋,不知有一种什么魔力,竟让爷爷巴达了一辈子。除了吃饭和睡觉,爷爷可以说烟袋不离口,口不离烟袋。甚至连打麦场这种严禁烟火的活计,他老人家口里也叼着烟袋。有时即使烟袋锅里什么没有,也不影响他巴达得有滋有味。一袋烟抽完,爷爷就像过了把瘾,人也陡添几分精神,对我们打开话匣子:“我说当年哪……”。看着爷爷叼着烟袋香甜痴醉的样子,我百思不得其解,甚至怀疑里面装有蜜糖。有一次,趁爷爷不注意,我抓过来偷偷抽了一口,辣得直咧嘴,从此对爷爷的烟袋之谜更加深一层。
爷爷的一生是不幸的。他幼年丧父,中年丧妻并痛失两子(叔叔十几岁病故,大爷27岁被日本鬼子杀死),他老人家惟一感到欣慰的是与毛泽东同岁。人前时常提起,且引以为自豪。爷爷虽然不能与毛泽东开比例,但他老人家的勤劳、智慧、精干和坚强,却令我们佩服至深。正是靠着这些,他把一个原本穷得叮当响的十几口之家,操持着拥有了十来间房屋,46亩土地,一牲口,还有一处小油坊,成为村人羡慕的对象。虽然为此土改时我们家被划成“献田户”,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,但这一点也没改变他勤劳能干的秉性。他五十年代后期因最早实行科学种田,创下全村和全镇的高产记录,被评为县劳模和种田能手,受到政府的表彰。79岁的他叼着烟袋打轳辘,在村里传为美谈。
最难忘的是爷爷对我们的疼爱。他虽然没正经上过学,却打得一手好算盘,也识得一些字。有空就教我们写字,打算盘,还和我们一起玩耍。那些年,爷爷年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父亲在外面工作,我们兄妹年幼,家里没有劳动力,挣不到工分,自然成了缺粮户,日子过得很是拮据。尽管如此,每逢赶集,他老人家都不忘买点瓜果李桃之类好吃的东西,回家分给我们吃。而他自己从来不吃,说咬不动,实际上是舍不得吃。因此,盼爷爷赶集,盼爷爷回家,竟成了我们童年一桩幸福的事情。有时因分配瓜果大小不均,我们打了架,爷爷总是慈祥地笑着劝解:“不要争了,下次赶集我多买,让你们吃个够”。但是爷爷下一次赶集,买得依然不够多。
爷爷还有一大特点,就是特别爱说。这也难怪,爷爷年龄大,走的路和桥多,经历的事也多,加之本来就健谈,所以话也就格外多。不管在什么地方,他老人家只要一打开话匣子,就像春水泄闸,滔滔不绝。他肚子里似乎总有讲不完的故事,说不完的话题。为此,村人送他一个绰号——三千六百句。
二
爷爷一生讲得故事很多,有一个令我终生难忘。
那是我12岁小学毕业那年的春节。傍黑时分,全家举行的第一个仪式是请家神。爷爷提着篮子,里面放着供品和纸香,还有用火纸写好的先人的牌位,率领子孙们浩浩荡荡,走到村外,找一块平地,摆上供品和先人牌位,在地上画三个圆圈,每个圆圈上放一叠火纸,焚上香,点着纸,爷爷小声念道:“老爷奶奶,回家过年了”。然后面牌位而跪,虔诚地磕头。我们也都学着爷爷的样子,扑扑通通跪下去磕头。之后,爷爷收起牌位和供品,率领我们回到家里,将牌位和供品摆到堂屋的高桌上,算是将家神请回家中。后来,这一神圣仪式文革时期被当作“四旧”废止了。
请完家神,全家人围坐一起,吃团圆饺子。吃饱喝足之后,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院子里放鞭炮,女孩子则点起礼花金在院子里转圈圈。玩够了,我们回到堂屋,依偎在爷爷身旁,围着木炭火盆,听爷爷讲故事,等待“发码子”—即子夜时分,烧香磕头放鞭炮,祭把祖先神灵,辞旧迎新,家族之间互相串门慰祖。爷爷先是和大人们议论当年的收成,盘算来年的生计,有时也谈论些国家大事,张长李短什么的。所有长辈中,爷爷年龄最大,辈份最高,也最健谈,所以讲得最多。他每讲一阵子,就将烟袋含在嘴上,巴达几口。或许是新年的温馨祥和勾起了爷爷对战乱年代往事的回忆,或许是供在高桌上的祖先牌位使爷爷想起死去的亲人,这时他忽然长叹一声,说道:“现在的日子多好啊,多么太平!想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那会子是什么光景!”于是,爷爷给我们讲起了下面的故事——
1942年4月初,共产党领导的泰安县独立营端了徂阳县汶申庄的日本兵据点,消灭了一个班的日伪军,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品,埋藏在咱薛庄村一地主家的地窑里。聚集在大汶口的日本“红部”“红部”即时称日本侵略军驻泰安市大汶口的集中营获愁,密谋对薛庄进行报复性大扫荡,妄图夺回被我营缴获的军械物品。四月初三那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人们还在沉睡之中,50多名日本鬼子和100多名汉奸悄悄逼近了薛庄。你奶奶、你娘、你大娘、你姑姑等女眷们先行一步,逃了出去,我和你大爷、你爹则被敌人围困在村子里,急促的脚步声,日本鬼子叭哩呱拉的喊叫声,汉奸队的吆喝声,夹杂着警犬的狂吠,撕破了村子的宁静,给村子笼罩上一种凶险恐惧的气氛。敌人把周围没来得及逃出的600多村民围赶到村西北角一个场院里,四周架起机关枪,三步一岗,五步一哨,两条大狼狗伸着血红的舌头窜来窜去,很是吓人。龟田队长通过翻译官向人们喊话,要人们供出独立营缴获的武器弹药埋藏的地方。连喊几遍,没有一个人应声。敌人恼羞成怒,用刺刀逼着村民,一个一个往三间场屋里赶。想把全部村民赶进屋子,如果再不招供,就放火一起烧死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……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小茅屋已经挤得风雨不透,万恶的日本鬼子还逼着村民硬往里塞。谁不想进,或挤不进去,就用刺刀挑死。人们只能死命往里钻,没命往里爬,其结果必然是人踩人,人摞人,一层不行两层,两层不行三层,有点像杂技里的叠罗汉。不过这可不是什么供人观赏的娱乐节目,而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死亡杂技。最下面的不堪负重,被踩压得鬼哭狼嚎,哭爹喊娘。凶残的日本鬼子熟视无睹,充耳不闻,依然端着刺刀,逼着人们往里钻……
与此同时,另一伙敌人把我、你父亲、你大爷和几名村干部在你大爷家的院子里,逼着你当村长的大爷和其他村干部说出军械物品的埋藏地点。你大爷不说,万恶的日本鬼子就把你大爷捆到一张吃饭的桌子上,让汉奸用铁壶往你大爷嘴里灌辣椒水。你大爷闭着嘴不喝,汉奸就捏住你大爷的鼻子灌。灌一阵子,汉奸们把桌子立起来,让你大爷说。你大爷仍然不说,汉奸把你大爷放到地上,再灌。如是反复几次,灌得你大爷的肚子像西瓜,还是坚决不说。凶残的敌人一看这一招不行,就来更残忍的。他们把桌子重新放倒,让你大爷仰面朝天躺着,找来一块木板,放在你大爷肚子上,两名汉奸一人按住一端,用力往下压。辣椒水混着血水从你大爷嘴里往外喷射,痛得没命得嚎叫。我和你父亲不忍心看,都低下头。你大爷被折磨得昏死过去,汉奸就用凉水把你大爷浇醒,继续盘问。你大爷真是好样的,至死没吐一个字。气急败坏的龟田队长让翻译官问我:“你还要不要这个儿子?”我愤愤地回答:“我当然要儿子,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军械物资埋藏在哪里。”
这时,龟田队长就像一头急红眼的野兽,呀呀叫了两声,刷地抽出东洋刀,搭在你大爷的脖子上,往前一推然后猛一往回拉,只见你大爷的头就像西瓜一样滚出好远,血流如注。看到这惨景,一股热血直冲我的脑门,我真想冲上前去,和狗日的龟田拼个你死我活。但理智告诉我,这样赤手空拳和真枪实弹的鬼子搏斗,既报不了仇,也雪不了恨,只能多搭一条命。为平定激愤的情绪,我从腰间取出烟袋,放在嘴上,想吸几口烟,只听喀嚓一声,玉石烟嘴不知不觉被我咬了个粉碎。我不忍再看,索性闭上眼睛,任凭泪水顺着面颊汩汩流淌。
讲到这里,爷爷停了下来,从腰间摸出烟袋;颤抖着装上烟,点着,大口大口地抽着,一股股乳白色的烟雾,在屋子里弥漫,借着油灯,我看到爷爷皱纹纵横的脸上闪着两道泪光。
抽完烟,爷爷将烟灰在桌腿上磕掉,情绪也平静许多,又接着讲下去——
在相距不远的另一个院子里,一伙日本兵和汉奸把一位叫薛画文的青年手脚用铁丝捆起来,倒挂在屋梁上,下面点起大火,来回推拉着熏烤,逼他说出埋藏枪械的地点。那位青年说不知道,就一直熏烤下去。那位青年的脸熏黑了,头发烧焦了,皮肤烤糊了,人昏死过去了,可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还不依不饶……
村西北的场屋内,那场人世间绝无仅有的死亡杂技还在继续。
屋里的人叠摞得已经触到屋顶。最上面的人已经把屋顶顶破。
凶残的日本鬼子还不肯罢休,依然用刺刀逼着村民往里钻。与此同时,他们在场屋四周堆起玉米桔和麦草,浇上汽油……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要在徂徕山下的薛庄上演。
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,一个日本兵跑过来,对着一个小头目模样的鬼子叽哩咕噜了几句什么。只见那小头目朝在场的鬼子和汉奸一挥手,丢下我们,带走几名村干部匆匆离开了院子。各路鬼子汉奸都停止了侵害,集合起来,向西南方向匆匆撤去。
当时我们都觉得蹊跷,后来才知道,泰安县大队得知大汶口的鬼子血洗薛庄的消息后,命令独立营紧急集合;冲下徂徕山,从四面包围了鬼子。本想打歼灭战,但考虑到敌人装备精良,我军武器落后,若直接交火,势必死伤许多群众。鉴于这种情况,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人员派人与龟田队长谈判,告诉他已被独立营重兵包围。只要他不再杀害群众,自动撤出薛庄,我军将给其留一条生路。龟田不知我军虚实,考虑到自身安全,被迫接受。于是,我军在村西南方向闪开一道口子,放鬼子和汉奸出去,解救了全村百姓的生命。
鬼子撤走之后,乡亲们把你大爷的头和脖子用麻线缝合在一起,仓促安葬了。那一年,你大爷才27岁,他是为保护军械物资而死的,死得很惨,从独立营官兵到全村父老乡亲,没有一个不夸他是好样的。
故事讲完了,爷爷又从腰间取下烟袋,装上烟,点着火,抽了起来,边抽边感慨说:“如果不是共产党和八路军,我们家,还有整个薛庄,不知要遭多大难呢?后果不敢设想,现在能过上太平日子,过年能吃上饺子,我打心里知足。”
听爷爷讲完这个悲惨的故事,我当时一方面为大爷的死感到悲痛,同时心里产生好多不解:日本鬼子那么残无人道,为什么不狠狠打他们,把他们一口消灭光?我们国家那么大,人口那么多,为什么还要遭受小日本的欺负和杀戮?
爷爷抽完那袋烟,来到院子里,抬头看了一会天上的星辰,庄严地说:“时辰到了该发码子了。”我们顿时来了兴致,跑前跑后,帮着大人摆供品,点香烧纸,放鞭炮,然后跟在大人身后磕头,欢乐又回到我们中间。举行完这一隆重的仪式,我们回到屋里,盛上水饺,每人还分到一碗用粉条、白菜、油条和猪肉拌的凉菜,开始吃年夜饭。尽管猪肉很少,每个碗里不过薄薄的几片,但我们吃得又香又甜。
三
爷爷为之庆幸的平安日子没过多久,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。似乎一夜之间,一切都翻了个儿——出身革命家庭,时任良庄公社党委常委,对党忠心耿耿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,13岁的我因用弹弓打讲桌上的黑板擦,石子反弹到教室正前方的毛主席像上,也被打成小反革命。我和父亲分别戴着高帽子游街,不同的是父亲个子大,戴的帽子高;我个头小,戴的帽子小。我们父子被红卫兵押着,在大街上走着,后面是高呼“打倒”口号的队伍,两侧是围观的人群。或许正是众人的观看,使红卫兵们获得一种成就感,也激起战斗的豪情。为表示对走资派和反革命的愤慨,以显示自己革命,他们不时用拳头打我们一下,或踢我们一脚。那时我已经知道爱面子,当众受此羞辱和难堪,我感到无地自容,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然而红卫兵并不因此轻易放过我们,而生着法子,把我们往死上折磨。仿佛批斗得我们越狠,他们就越革命似的。我和父亲不论回家多晚,都能看到爷爷的烟袋一明一灭。为了不让爷爷担心,我和父亲都努力装出没事的样子,爷爷似乎也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,但我明显地发现,一向爱说话的爷爷变沉默了,人也似乎一下子苍老许多:脸上的皱纹变得璨深更密,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,本来硬朗的脊背变得有点驮,烟也抽得更勤了。有时我都睡醒一觉了,黑暗中,还看到爷爷的烟袋锅一红一灭,并听到他自言自语:“唉!好不容易赶走日本鬼子,过上太平日子,又搞什么运动啊?日本鬼子已经要了我大儿子一条命,这一次难道还要我二儿子和孙子的命吗?想过平安日子怎么这么难?”
尽管后来落实政策,给我们父子平了反,父亲恢复了工作,我也重返学校读书,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但经过这场动难,爷爷的确苍老许多,烟袋在嘴上叼得也更勤了。
四
10年之后的1976年,我已经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。那是7月,总部派我去成都调拨一台大型设备(提升倦扬机)。临行前,我回家向爷爷告别,不料爷爷病重卧床,父、母、大娘、姑姑等人都守在爷爷床前。此时的爷爷面色蜡黄,眼睛深陷,显得非常苍老和虚弱,但依然那么慈祥而和善。看到敬爱的爷爷病成这副样子,我鼻子一酸,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看到我回来,爷爷脸上掠过一丝笑意,用微弱而含糊的声音说:“孩子,你回来了。
我抹去眼泪,强作笑颜,伏下身子,动情地对爷爷说:“爷爷,你孙子回来看你老人家了。”本来是向爷爷告别,可告别的话在嗓子眼里打着滚说不出口。
爷爷知道我要出差后,一点没生气,反而高兴地说:“俺孙子长大了,能为国家干事了。”歇了歇,又对我说,“去吧,放心地去干吧!好好干,别误了公家的事,家里有你爹娘他们照顾我就行。我没事,会好起来的。”
听了爷爷一番深明大义的话,我更加难过,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,簌簌地流下来,我怕爷爷看见,赶紧把头扭向一边。
这时,只听爷爷又用虚弱的声音说:“孩子,给爷爷装袋烟,我再抽一袋俺孙子装的烟。”我拿起爷爷的宝贝烟袋,给爷爷装好烟。父亲扶爷爷坐起来,我把烟袋放在爷爷嘴上,用火柴给爷爷点着。爷爷颤抖着嘴唇,只吃力地抽了一口,就再也抽不动了。
我知道爷爷病得不轻,我这一去,回来能否再见到爷爷都说不定,我实在不忍心在这种时候离开爷爷,但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离开。此时,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,什么是生离死别。我告别爷爷和家人,怀着复杂的心情,拖着沉重的步履,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家,踏上去成都的路。离家乡愈远,我对爷爷的思念愈深。当我圆满完成单位交给的任务返回家乡,已是一个月之后。一进家门,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下子攫住我的心。见到母亲,我第一句话就是:“爷爷怎么样了?”
母亲沉痛地说:“你再也见不到你的爷爷了,他老人家在你走后第九天就去世了。”
可怕的预感终于得到证实,一种撕心裂肺的悲痛使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蹲到地上放声大哭,爷爷疼我爱我的一幕幕往事,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闪现。想到爷爷生前对我的疼爱,再想想自己在爷爷病重的时候离开,没能尽孙子的孝心,心里就更加难过,哭得也更加厉害。
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爷爷以其84岁高龄,与毛泽东同年去世,九泉之下的爷爷肯定又将为此骄傲和自豪。但愿这骄傲和自豪能多少抚平爷爷一生遭遇的坎坷与不幸,给爷爷的魂灵带来慰藉和光明。
我来到爷爷的坟茔,采集一束鲜花,放到爷爷坟前,然后虔诚地跪下去,给爷爷磕头,想到勤劳的爷爷,慈祥的爷爷,整天烟袋不离嘴的爷爷,已经化作一掊骨灰,长眠于此,今生今世,将再也见不到他,我心如刀绞,悲痛欲绝,泪流满面,哽咽出声,长跪不起。
回到家里,我独自走进爷爷的房间,凝视着爷爷睡过的土坑,呆呆出神,往事如缕,思绪万千。无意中一抬头,我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伴随了爷爷一生的烟袋,感觉就像看到爷爷一样亲切。
我想,这恐怕是爷爷留给我们惟一的、而又是他老人家一生最心爱的有形遗产了。
我反复又想,爷爷留给我们的遗产又太多大多了,刚直不阿的硬骨头精神,自力更生、艰苦朴实的作风,勤劳勇敢、精打细算的治家本能等等等等一切精神财富,这都是留给我们并激励我们奋进的无价之宝和最宝贵的财富。
我深切地叹悼爷爷,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,子孙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平凡、伟大!
此时,我才真正知道爷爷一生用烟袋解愁的真正奥妙了……
直至现在,爷爷叼着长烟袋的镜头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老人家慈样的面孔和他讲的国难家难的故事一样,终生难忘,激励后人。
泰安诚信达经贸有限公司
总经理:薛玉利